武岡密碼之十 石牌坊之冬
作者:曹潺觀察

綠楊芳草長亭路,年少拋人容易去�����。四十幾年過去了����,當(dāng)人們津津有味閱讀我的文字時,便有了對文字補充的熱忱����,彌補我記憶曾經(jīng)的缺失,我的少年生活變得更加清晰與鮮活�����。
過去石牌坊的冬天是頗為寒冷的����,一條青石板路延伸開去,首接四牌路��,尾甩河灘坪。馬路兩邊���,木板屋相依相偎���,生存著古城善良的人們。大米廠����,印刷廠,郵電局與中醫(yī)院�,擠在這條人口稠密的青石板街道上,更加增添了這條街道的喧鬧�����。

沿著一條幽暗密閉的木走廊走進去����,便進入杜家薈���。走廊首尾顯亮���,中間確實有點暗,因為筆直,自然不必?fù)?dān)心磕碰�。
杜家薈一天井一堂屋,面積不大�����,住了十幾戶人家��,朝夕相處�����,親如一家�。
天井的大小是由四方木屋的屋檐決定的,若形容杜家薈的天井大小�����,說既不大也不小適宜�,只是檐邊離地面矮了些。
冬天的杜家薈逃不出小城的寒冷�����。

幼時的杜家薈�����,鵝卵石鋪就的天井,若凹處積了水�,寒夜一過,水便冰住了�����,薄薄的一小片���,在冬陽的照射下��,有了色的光�。再抬頭�,檐口處,奇跡般吊了尖削的冰尖����,垂向地面,圍住天井的屋檐���,吊了一圈�,寒冷把杜家薈困住了�,露出崢嶸來。站在條凳上�,伸手便可折下冰柱了,長若八九寸�����,往口里一含��,有夏天吃冰棒的感覺�����。
穿過木走廊����,走過天井與堂屋,院后住了兩戶人家�����。再走�����,便是一大片菜地���。冬天的菜地�����,少有掛果�����,只有枯藤�����,乏力地繞著竹竿����,小城的寒冬,降服了萬物�����。

何時杖爾看南雪���,我與梅花兩白頭�。梅花雖有���,朔風(fēng)之中�����,終究還是孤獨了些�。杜家薈的人們�����,秋暮落盡����,早已采辦了木炭,為抵御嚴(yán)冬��。寒冷如約而至����,火桶與火柜便可派上用場。
火桶與火柜是小城人們抵御酷冬的玩什�����?��;鹜坝写笥行?���,方型,小的火桶是可以提來提去的��。一個小木盒上有一個小提手���,木盒里有一個掉碴的土陶碗���,碗里燃了炭。提在手上�,竄門,上街���,上學(xué)����,出工��,用得著���。
我的小學(xué)是高廟���,冬天����,背著書包����,戴著軍棉帽��,提著小火桶����,走到杜家薈的后院,后穿城河�,后化龍橋,后和合街�,爬六十幾級臺階,便到了高廟小學(xué)�。

仍然記得寒冬過去,高廟里那幾株槐樹葳蕤的樣子���,一廟槐花的清香�,擠滿了懷舊的鼻腔。
哦��,忘了告訴你��,我是21班的��。近50年了����,提在手上的火桶,以及非仰脖才能見的滿白的高大槐樹���,那是春天里的記憶��。
火柜是什么呢��?這樣形容吧�����,一張倒立的八仙桌�,全封住���,腳凳底四方用木板相連��,上空����,四塊木板安放臀部。下放置一大火盆�,盆上有一柵欄似的木框,坐木板�����,腳踩柵欄���,五六七個人,圍坐���,上蓋花格被�����,從頭到腳�,直達(dá)心扉���,暖了個透�。

石牌坊人,一到冬天����,大姑娘小媳婦,喜歡彼此吆喝��,到我家火柜里來烤火吧����,一烤,從晌午到黃昏��,還真是眨眼之間�。要知道,姑娘的那點心思�,里三層外三層的裹著,亦可里三層外三層的揭開�����,說盡道明頗費周折的�����,時光便在溫暖的炭火邊溜走了�����。
石牌坊的人們,寒冬之間�,套了近乎,深了感情���,歲月只在庸常里了��。
去年寫的《武岡往事之石牌坊》��,漏了幾戶人家��,歉意了��,一并補上:郵遞員老劉家�����,一唐家,胡家���,膏藥奶奶家����,司機劉家,電影蔣家����,還有一蔣家,賀家�����,我家����,映雯小妹家,肖家�����,戴家�����,院后一唐家一蔣家���。之所以這么補充�,是想讓我曾經(jīng)的鄰居永遠(yuǎn)在我的文字里留存下去���,能做鄰居�,前世要修一千年的。
小城點點愁���,明月人倚樓��,石牌坊的少年生活�,就讓它留存在我的文字里吧��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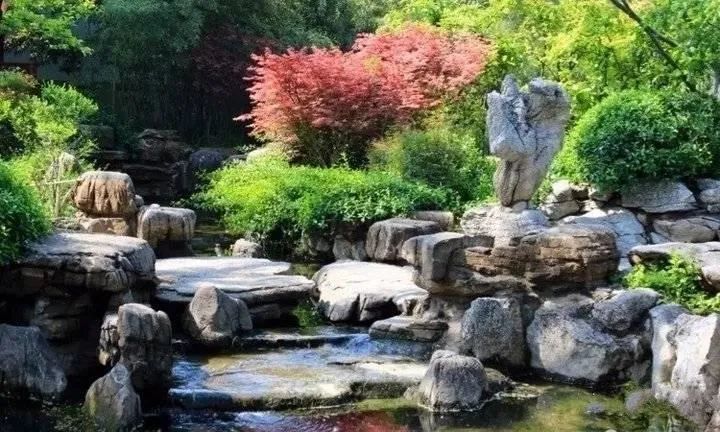
(請關(guān)注公眾號)

免責(zé)聲明: 本文內(nèi)容來源于曹潺觀察 ����,不代表本平臺的觀點和立場����。
版權(quán)聲明:本文內(nèi)容由注冊用戶自發(fā)貢獻(xiàn),版權(quán)歸原作者所有�,武岡人網(wǎng)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(wù),不擁有其著作權(quán)����,亦不承擔(dān)相應(yīng)法律責(zé)任�。如果您發(fā)現(xiàn)本站中有涉嫌抄襲的內(nèi)容���,請通過郵箱(admin@4305.cn)進行舉報,一經(jīng)查實�����,本站將立刻刪除涉嫌侵權(quán)內(nèi)容���。